div>
表1 传统规划体系空间用途管制特征
3.传统规划体系下空间用途管制的问题
传统规划体系下各部门分管分治模式存在许多难以协调和解决的问题,空间用途管制效力较为低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分管分治难以形成合力,统筹管制缺失。传统规划管制体系以“横向部门+纵向分级”结合为形式,将空间资源分属于国土、城乡建设、农业、林业、水利、环保等部门进行管控,各部门各自分立、互不关联,难以形成合力,出现职责不清、法规界定不明以及空间管制缺位、越位等问题。在规划统筹上,基于事权主体管制的空间规划,在规划平台、编制标准、制度、方式、目标、分类及侧重点等方面难以统筹协调,同一空间面临“都管等于没管”“没人管”的困境。
(2) 用途管制未能全覆盖。各类规划管制通过划定功能区的方式分类确定开发利用条件,但因划定标准和侧重点不一,未能实现空间全覆盖及有效管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侧重建设用地与农用地之间的转换管制,忽视了未利用地;城乡规划管制侧重建设用地的管控,忽视了建成区之外的用地;生态资源管控侧重耕地、林地的管控,忽视了低等级的园、林、草、水及其边角地带等,导致空间破碎化、孤岛化现象严重。
(3)缺乏统一有效的分区及许可制度。四类管制模式分区标准及空间定位不一,如城乡建设用地管制采用“三区四线”模式,土地用途管制采用“三界四区”模式,生态资源管制采用“单要素管制”模式,主体功能区规划采用“四区”模式,导致划定边界交叉、遗漏,管制“真空”、空间用途冲突等问题;同时,实施“单要素管制”的生态资源管制割裂了“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目前,成效较为显著的实施许可制度包括建设用地管制的“一书三证”制度,以及土地用途管制的耕地及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其他各类空间的用途管制制度不够完善,约束力较弱,管制效率低下。
(4)未能建立全过程监管的监督体制。现行制度“重量轻质”“重审批轻监管”,缺乏监督管理手段,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未能实现全过程管制。
(5) 管制体系的完善程度不一。城乡建设用地和土地用途管制手段多样且有效(分区分级管制、指标管制、用地管制、项目审批和监督管理),管制体系较为健全;生态资源管制体系以“总量控制、定额管理”等规模指标为主,未落实到空间主体,管制手段单一,约束力较弱;主体功能区规划未能有明确有效的管制手段。
(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统一管制阶段的内涵与特征
1.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空间用途管制的内涵
为解决上述问题,中央政府深入推进管理体制改革,在2014年推动“多规合一”的背景下,多部门联合要求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开始了探索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阶段。2017年多部门联合起草《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将用途管制扩大到所有生态空间,标志着统一用途管制探索步入新阶段。2018年,随着自然资源部整合多部委的规划职能,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将三条控制线由过去多个部门各自划定,转向由自然资源部统一划定、管控,并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三大核心环节,有效解决传统规划体系阶段空间规划政出多门、交叉矛盾、合力难及效力低等问题,标志着国土空间管制进入了机构、权责、依据与方式统一的新阶段(图1)。
图1 国土空间用途全生命周期管制框架图
三条控制线作为独立要素被提出,已有很久的历史;作为整体系统被提出,则出现于2014年、2017年提出的完成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划定工作。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实施监督的若干意见》《指导意见》确立了“三线”作为我国空间规划体系自上而下刚性传导、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核心工具(图2)。其中,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永久基本农田是按照一定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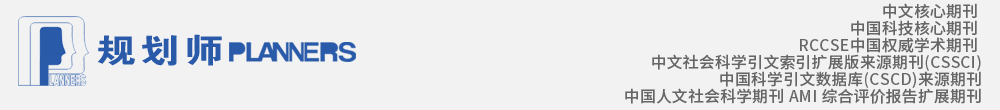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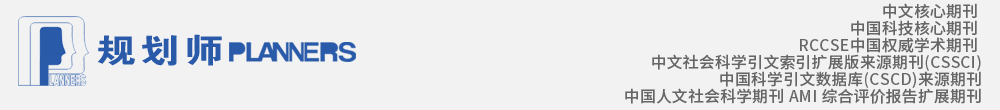
 首页 >
电子刊物 >
文章分享 >
首页 >
电子刊物 >
文章分享 >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0195号
桂公网安备 45010302000195号